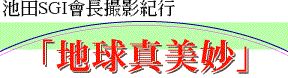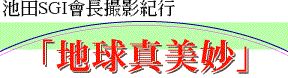城塞的市鎮–盧森保
呈現不可思議景觀的市鎮。
一到盧森堡,眼睛就不禁「上下移動」。因為整個市鎮被
建造在懸崖峭壁上。每定幾步,就可「俯視峽谷」。所以橋
也特別多。橋的高度還會讓人暈眩。
聯繫新、舊兩個市鎮的「阿道夫橋」,有46米高。直到下
面的河川,所有崖壁被森林綿密地覆蓋著。
整個市鎮浮在宛如切下來的雄大空間中。
◆
200年前,歌德也對這裡的景色驚嘆道:這個市鎮「偉大
中帶有優美,威嚴中帶有可愛」。
43歲時的歌德,因投入與法國革命軍的戰爭而來到此地。
「盧森堡」是「小小城塞」之意。法國革命軍雖攻打半年之
久,然而,與斷崖渾然一體的城堡,固若金湯,屢攻不破。
◆
我也是由德國來到此地。
從歌德的故鄉–法蘭克福,乘車到可布連茲鎮,再搭兩小
時的火車才抵達。
鐵路沿著萊茵河的支流–摩澤爾河伸展。有時會在右側看
到中世紀的城堡,有時會在左側看到摩澤爾酒的葡萄園。
當摩澤爾河從車窗消失時,就到盧森堡了。那天是1991年
6月9日。可看到放牧的牛群。草地由深綠變成翠綠。
面積相當於日本的神奈川縣。人口約有40萬。其中三分
之一是外國人。
這個被德、法、比利時圍繞的小國,其國民所得在歐洲是
數一數二的。也是僅次於倫敦的歐洲金融中心。
◆
當時,作家艾特馬托夫氏正擔任蘇聯駐盧森堡大使,而駐
在此地。雖以逗留短短兩天,但拜訪大使館時與大使一家人
的交談,成了快樂的回憶。
◆
說到文豪雨果也屢次造訪盧森堡。
1871年69歲時,雨果亡命到靠近盧、德邊境的維恩登市。
在巴黎,左翼共黨與政府軍持續著以血洗血的紛爭。
「能解決問題的,不是大砲,而是愛!」
詩人的這人道呼籲,遭到雙方的攻擊。
友人們被捕與處刑的消息,陸續傳到身在比利時的詩人雨果那裡。
接著是暴徒向門窗丟石喊叫:「殺掉雨果!處以絞刑!」
◆
被比利時政府驅除出境的雨果,於是轉往盧森堡。
「直到今天,我都只說真實。其他的一概不談。只有不斷訴
說其實。然而也因此總是遭受攻擊。世上還有比這個更不愉
快的事嗎?」
火車一路搖晃,到達車站是晚上7點。等待著詩人的,一
反常態,是民眾的歡迎。「雨果萬歲」、「共和國萬歲!」
這個國家的民眾知道真實、支持真實。不論權力者如何一
味地「隱瞞真相」。
◆
在大自然中勤奮工作的詩人雨果家門前,每到早上,人們
就來為他演奏音樂。
夏日的某一大,有位老農夫來了。
老人脫下帽子,高喊著:「願榮耀降臨維克多雨果!」然後朗
誦起雨果的詩來。
「即使只剩一千人,好!找也要留下來堅持到底!
即使只剩一百人,我還是要反抗修羅(反動權力者)。
如果剩下十個人,我會成為第十個人。
如果只剩一個人,那一個人就是我!」(摘自潮出版『雨果詩集』)
◆
這個「執念」正是「難攻不破之城塞」。
正因有這份「心」,才能在列強的狹縫中生存至今。
◆
在被納粹德國攻入時,該國「抗暴運動」的英勇事蹟也非常有名。
納粹推行該國的「德國化」。不久又強行「國籍、語言與人
種」的國勢調查。
那就是相當於「蹈繪」。如果不全部照著納粹的意思回答說
「德國」等,就會被帶到強制收容所。大家被逼得走頭無路。
只有仰天長嘆。
就在那時,一張字跡潦草的小紙條在國民之間迅速傳開。
「三項都寫『盧森堡』!」
如電擊般的這一句話,讓百姓紛紛下定決心。
納粹也無法逮捕萬眾一心的全體國民。
◆
我下了往溪谷的長長斜坡,沿著溪邊走了一會兒。
如今歐洲共同體的各種機關,都集中在這個受盡戰爭之
苦的城塞都市。
正因為一向受到大國的欺壓,對「歐洲合眾國」的企盼也
最強烈。
◆
從幾十公尺深的溪谷往上看,好幾座古代尖塔,仰慕太
空的永恆而聳立著。
願人心也如這個太空。
雨果的『九十三年』書中一節掠過腦際。
「我所說的共和國,是帶領民眾走向『藍天之下』的國家」。
◆
返回溪谷上方的市區時,看見廣場上有一群孩子在追逐嬉戲。
「未來」的明朗聲,在2000年古都的石壁上回響,悅耳、動聽。
(「攝影紀行」到此全部完畢,感謝各位讀者的支持)
奧地利藝術家協會的漢斯邁亞會長談到:「池田先生自謙
不是技術卓越的攝影家。但是傾注在先生作品申的是『心』、
是『本質的東西』。
如今,或許可以說攝影是通達世界的『語言』。攝影也被運
用在學術上,來發現映入人們眼簾的世界。
但另一方面,先生具體地讓我們看到,攝影並非只為了
『認識事物』,而是為了『表現心及永遠的本質』」。
(編譯自1999年8月29日聖教新聞)
|
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