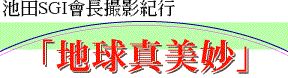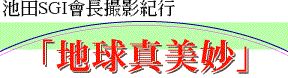巴哈馬的哥倫布塑像
「樂園」是什麼?在哪裡呢?
假設地圖上有「樂園」這種地方,巴哈馬群島想必是其中之
一吧!
甚至有人說:「沒有來過加勒比海的人,是不曾懂得其正
的『色彩』及真正的『光』。」
◆
珊瑚礁的海,常夏的氣候,結實纍纍的果樹。行人的衣裳
也是橘色、黃色、藍色、紅色、深紅色。大自然、街道都
是爛漫的熱帶性色彩。
顏色本身歌頌著「生命的讚歌」,整座島洋溢著令人身心
舒暢的祥和氣氛。
為芝麻小事焦燥、煩惱的「灰色面孔」者,在這裡也會感
到羞愧吧!
為了紓解在塵囂中的疲憊,據說一年有300萬人來此地度假。
◆
3年前造訪古巴之際,當時與古巴持續著緊張關係的美
國,沒有直飛古巴的班機。結果,便在佛羅里達外海的「巴
哈馬」首都拿騷過境。
雖只停留短短幾個小時,卻成為我的第52個訪問國。
飛機從邁阿密飛近島時,海色開始變化,像是弄碎、溶化
無數藍寶石般的高貴藍色,彷彿手一伸入就染成深藍似的。
還有白色沙灘及種著椰子樹的海岸。
◆
500年前哥倫布到達「新大陸」,第一站就是巴哈馬群
島。「這座島是人們眼中最美的…青蔥的大樹枝葉扶疏,
鳥兒合唱出悅耳的和聲,任誰都會流連忘返。」
但是,「發現新大陸」這件事對原住民來說,是非常不幸的
遭遇。
暫且不談哥倫布的意向,同行的白人其行為之殘虐,只需
稍微描述其中一小部份,就叫人躊躇不前。
從島民母親懷中搶去嬰兒當面餵狗,諸如此般的「惡魔」陸
續蜂擁而來。「樂園」轉瞬間變成了「地獄」。
原住民在強制勞動、傳染病與絕望中,僅僅半個世紀後就
絕滅了。現今的巴哈馬人,多數是17世紀時由非洲被當作奴
隸帶來的那些人的子孫。
◆
拿騷的港口有大型遊艇並列著。市中心有觀光用的四輪馬
車,馬兒戴著可愛的花帽子。
建築物的牆壁也是黃色、紅鶴色,是道地的加勒比風格。
巴哈馬人口約28萬人。此地也有我們SGI(國際創價學會)
的會員。
生活在這樣美好的天地,是何其有幸!當地會員在己心之
中,擁有比什麼都廣闊的「樂園」。
我對友人致贈鼓勵的話語:要成馮人生的勝利之王、幸福
之王。之後,再度奔向機場。市場內有堆積如山的麥桿製
品、T恤、民藝品。精力充沛的歐巴桑們(婦女),拉長了喉嚨叫喊
著:「便宜的喔!便宜的喔!」她們的皮膚是褐色,高頭大
馬,笑容滿面,身上配戴著花俏的裝飾品。
她們被尊為「巴哈馬媽媽」,以勞動者而聞名。想像不出她
們悶悶不樂是什麼樣子。我想她們縱然有勞苦,也總是面帶
笑容,主動的「向人打招呼」。
相信只要有這份精神,「樂園」就存在這裡。因為幸福是
由心靈的互動產生的。
◆
我從行進的車中,按下快門,拍下街道上那棟粉紅、白
色相間的建築,這建築有巴哈馬、英國、美國風格摻雜其間
的感覺,據說是歷代英國總督的官邸。
巴哈馬曾是海盜船的據點,後來成為英國的殖民地,於
1973年獨立。作為英國聯邦的一員,如今的元首仍是伊利莎
白女王。
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,以「捨王冠之戀」聞名的前愛德華八
世(溫莎公爵)與夫人,即是住在該館。
◆
哥倫布的塑像仰望著天空,有點做作,不知他正在想些什
麼呢?
他橫渡大西洋,帶來了地球的一體化,同時也帶來了意想
不到的悲劇。
如今若要談他的光榮,並非在「幸運到達」這個結果,而是
在向著未知航路「毅然出發」的勇氣吧!
據說他的出航,是得到為逃避迫害而尋求新天地的猶太人
的支援。
在眾人皆反對、責備、躊躇當中,只有一個人說:「總得
有人去,不用怕!」而準備開航。當時他的生命洋溢熱情。
那股熱情就是他人生的「樂園」。
◆
在歐洲,還曾有人認真議論著:「印第安人!到底是人?
還是動物?」如今這已是笑話一則,然而五百年後的現代,
仍存在著思想、宗教、種族的差別。為了讓它在將來也成為
笑話,唯有靠「坦誠的對話」、靠「不同文化問的交流」。
別因芝麻小事而撈叨,心要如大海原般寬闊。只要有一人
立起,時代就會因此而改變。這是給現代人的「哥倫布之教
訓」吧!
◆
此地能否成為「樂園」,是「依人而定」、「依心而定」。
我一邊思索此事,一邊飛向正陷入孤立、苦難的古巴。
社會科學院院長莎姆耶魯梭利亞先生,在觀看過名譽會長
在玻利維亞的特魯巴利耶大學舉辦的攝影展後談到:「池田
先生的攝影,有今生命感動的內涵,並非只是生活的引導,
而是告訴我們何謂『為和平而生、為幸福而生』。
池田先生的作品是由『光』和『影』構成。尤其給予『光』是
其特徵。『光』是希望、是良識。作品彷彿傳來這樣的吶
喊:要活在那個光之中啊!」
(編譯自1999年8月7日聖教新聞)
|
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