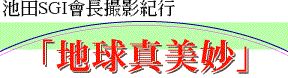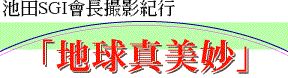上高地的水鏡
風景與人也有「邂逅」。
大自然生生不息,不斷變化,同樣的景物,每次看也都
不相同。觀賞景物的人也是生生不息,時時刻刻在變化。
不論是景物或觀景的人,都是短暫人生中僅有的一次相遇。
◆
我和「上高地」也是這樣的「邂逅」。
有一天,據報颱風將來襲。當時我在長野研修道場。「很
危險」!我要參加研修的會員趕緊去避難,我也轉往松本。
因為土壤的關係,道場內樹根很淺。本來認為沒問題,結
果卻如我擔心的,許多樹木傾倒。這是1982年夏天的事。
◆
在松本舉行一連6天的研修會。其中一夫,我訪問了上高
地。「錯過這個機會,就不知何時才能去」,無論如何我都
想去看看安曇一帶的會員。
在那3年前的夏天,長野有3000位代表聚集到研修道場
來。當時我剛勇退會長之職。
大家一起合影留念,上高地的會員也在其中。「總有一夫
一定去拜訪」,我心想一定要履行這個諾言。
而且,找他想為一起在松本的友人創造回億。因為「充滿
美好的回憶」這就是能說出「真正美好人生」的秘訣。
◆
從松本經過波田町,到安曇村。安曇三水霸之一的「水殿
水霸」旁,有當時梓川支部的會員在等候。
男女老幼,不論怎麼樣的面孔,都刻劃著一份純樸與堅韌。
我想這是每天仰望高山,和山談心的緣故吧!近天而居帥
人,相信心也會變得高潔吧!
牧口首任會長曾說:「山是人物的育成所」。
◆
據說,瑞士的裴斯泰洛齊以及其他近代偉大教育改革家,
大都是「在山國長大」。
「日本的瑞士是信濃吧!」不但形成日本群島的「絕頂」,教
育也最普及、進步,人人栩讚。
的確,長野地方似乎通情達理的人較多。
合影留念並稍談片刻後,我們造訪了上高地
「遂道」的黑暗一掃而空,眼前呈現另一種世界。左手邊有
一條翠綠色的溪流,那是梓川。不一會兒就看到大正池碧綠的水面。
聳立在池子上空的,是披上鮮綠衣棠的穗高岳。山麓飄浮
著雨後的白霧。景色散發出宏大卻平易近人的魅力。
我暫且下車,站在大正池邊。池鏡懷抱樹林倒影,閃耀
著翡翠色的波光。時光彷彿停止不動。
大正池一如其名,是1915年6月6日因燒岳火山爆發,噴出
的泥漿堵住梓川,而在一夜之間形成的。
河岸的樹林沈入水中,水面有乾枯的樹叢林立,呈現這種
不可思議的景觀。
這天因颱風剛剛過境,所以沒有那麼雜
亂,但據說這一帶每到旺季的夏天,每天存上
萬多人蜂湧而來。
人為什麼如此迷戀山呢?
◆
日本是山國,國土有七成是山林,但極少人
在拚命守護這些山。我經常在想,如果沒有森
林,會成什麼樣子呢?
所有河川會乾涸吧!潺潺流水是因為森林把
雨水貯存為地下水的緣故,而且還過濾得很乾淨。
若無森林,大地也會貧瘠吧!田地的土壤本來就是森林
造就的。
森林甚至也養育河川、大海內的魚兒。因為它將養份高、
溫度適中的水送到河口。
森林把海水生成的雨水聚集起來,形成河川、大海。在這
個循環當中,魚、獸、花、鳥和人,才得以全部活下來。
◆
那麼,造就如此偉大森林的是誰呢?就是山上的那些人。
不論怎樣的山,都有不畏辛勞地去植樹、育樹、運出木
材,並與樹木共生的人。他們甚至考慮到幾代後的子孫。
上高地的村莊,從江戶時代開始,就承包著危險的伐木工
作。但是,就在日本人忘記對山上人們的感謝、喪失活用大
自然的智慧時,日本的山川、海洋便這樣荒廢殆盡。
幾隻野鴨悠閒地滑著水,大正池的水鏡掀起陣陣波紋。水
鳥的生,枯木的死,生死都是生。生死一起唱頌生命之歌。
此情此景,瞬間帶來永遠令人懷念的某種敢示。
不論是誰,心中都有屬於自已的風景。或許是為了和這個
自身心湖所懷抱的風景相遇,所以人往山上去。
◆
山是人。
大自然是人。
風景是映照人心的鏡子。如同庭院映照那一家人的心,風
景照出該國的人心。
所以找不能不祈願:「為了日本人的心能蘇生,日本的河
川!蘇生吧!森林!蘇生吧!大地!蘇生吧!」
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的董事長張鏡湖先生談到:「自古以
來,中國對於優秀藝術都是以『詩中有畫,畫中有詩』作為最
高評價。
池田先生的攝影的確盡在此一言中。面對作品而感覺王維
或陶淵明的詩蘇生起來的,當不只我一個人吧!
當然,攝影和繪畫不同,但一流的作品都會綻放出射入心
坎般的光芒。它把我們導向更高的精神層次。
更達到大自然與人相互輝映的境界。這叫做『天人合一』
吧!彷彿傳來天道韻律與人之生命的共鳴音。」
(編譯自1999年8月1日聖教新聞)
|
 |
|